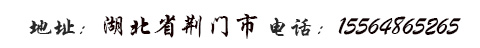道之北生产村的大院岁月
|
上世纪六十年代,家住西安道北生产村。道北这个地方从民国起到新中国成立,就集中了大大小小不少工矿企业,有纺织厂、丝绸厂、矿山机器厂,还有煤球厂等等。外人一听生产村名字像是农村,其实这里居住的大都是铁路和附近工厂的职工。村东是崇明路,村西是铁路东村,村北是生产后村,村门口南边的路叫二马路。 二马路是生产村居民每天出入的必经之路,这条路是道北地区最著名、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条狭长的小街道。二马路拓建于年,因为南侧的自强路曾经叫“一马路”,就顺称之“二马路”,本尊大名“复兴路”居然没有人知道了。 在儿时的记忆中,二马路这条狭窄破烂的小街道很长很长,东起纱厂街,西到北关正街,小时候从来都没走完过它。当年从河南逃难到西安的人,在这里落地生根,搭棚盖屋,狭窄的空间无法向四周扩展,只能纵向向上发展,逐渐形成了外观上高高矮矮、盘根错节的棚户区。 二马路的东侧,道北的一条主干道自北向南穿过,叫“太华路”,路东就到了大华纱厂地段,那里有一条纱厂街,是正经八百的“棚户区”。生产村的北面是生产后村,它就像二马路上的大杂院一样,都是一些高矮不一的自建房。生产后村黄河家属院门口,早年有一个臭水塘,夏天的时候臭气熏天,蚊虫泛滥,上世纪70年代搞爱国卫生运动时才把它填平了。 五十年代末,我的父母在道北太华路的西安黄河棉织厂工作,这个工厂是五十年代初新建,当时叫做公私合营,主要生产床单、毛巾等。黄河棉织厂给部分已婚职工安排了位于二马路生产村的“公租房”,现在叫“廉租房”,每月房租四元六角。 黄河棉织厂子校七六级学姐蒲公英记忆中的生产村小区平面图 生产村始建于年,一排排带院子的平房,像军营一样整齐排列,纵向四排,每排有八至十七户不等,第一、二排靠东,就叫“东村”;第三、四排靠西,就叫“西村”。房子全部坐北朝南,正房十四平米,房门正对面是一间只有三平米的厨房,厨房背后南侧则是前一排人家的正房。 生产村房屋墙体材料不是砖头,而是土坯。把半干的黄土装入模具,用石夯打实,打出来像砖一样的土坯,自然晾干后用以垒墙,外面用掺有碎麦秸的泥浆抹平。房子的樑和椽均为木质,顶棚为秸秆,其上再铺上小青瓦片。 左起:年11月,我,张彪,韦钢,地点:西安市新城区二马路生产村韦钢家门前。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照相馆以外的地方照相,还把眼睛闭了。摄影者是韦钢的哥哥韦炜。左起:年11月,张彪,我,地点:同上,这一张眼睛睁开了。摄影者是韦钢的哥哥韦炜。像当年道北许多家庭一样,我们家也是三代同堂,奶奶、父母、我、两个妹妹,一家六口蜗居在生产村十四号院七号一间狭小的平房内。 十四号大院十一间房屋,居住了十户人家。大院门坐东向西,从西往东,一、二号郭家,女主郭妈,黄河棉织厂准备车间工人,儿子狗旺,两个女儿秋霞、爱霞;狗旺哥已经参加工作,在建筑公司上班,秋霞、爱霞两个姐姐是院子里弟弟妹妹们的孩子头,我们这些小屁孩都喜欢跟在她俩身后。 三号高家,男主高伯书田,西郊三五零七工厂上班,女主翟姨莲花,一头卷发,黄河棉织厂织造车间挡车工,四个孩子,长女国庆,与一号爱霞同班,都在黄河棉织厂子校上学。后来翟莲花阿姨调动到三五零七工厂工作,高家就搬走了。 四号籍家,男主籍叔,和蔼可亲,很喜欢和小孩子说话,女主齐姨秀珍,与三号翟姨同事,两个儿子小衞、小衡。小衞与我同岁,成为院子里形影不离的小伙伴,一同进黄河托儿所,一同进黄河棉织厂子校上学。 左起:韦钢,籍衞,我,施学平(年5月14日) 难得的我与籍衞同框照小衞从小就机灵聪颖,用大人的话讲,猴精猴精的。春节放鞭炮,是男孩子的最爱。他把炮仗可以放在任何他想放的地方,扣在缸子下,塞在冬贮菜的大白菜里,我捂着耳朵,看着他点火,爆炸,搪瓷缸子飞上天,大白菜炸开了花,真是开心极了;夏天,我俩去八府庄玉米地里捉“油葫芦”,被看守的农民大伯发现追赶,他跑得飞快,一溜烟就没了踪影,我跑在后面,不轻不重挨了一脚,现在想起还心惊肉跳。 上学后,我和小衞始终未在一个班,小学时,他在2班,我在3班,四年级重新分班,我在1班,他又到了4班,直到中学毕业。 五号,女主陈姨玉梅西安第一丝绸厂工作,女儿花丽,似与我大妹珍珠同岁。 六号宋家,男主宋伯杰亭,黄河棉织厂会计,打得一手好算盘。宋大伯有一句名言至今记得:人越有钱就越省钱。比如有钱人有车坐,雨天出门不用打伞和穿胶鞋,而穷人就要多花钱买伞买胶鞋。宋大伯有五个孩子,两男:斌、惠敏,三女:宣芳、惠芳、春芳。 八号高家,男主高叔我曾写有《八号高叔》,此处不再赘文,女主张银花,黄河棉织厂准备车间工人,两个女儿。 九号搬走较早,已经记不清,略过。 十、十一号孙家,孙爷爷两口与三女儿,孙子宗亮、外孙女小丽。听大人们讲,孙爷爷天津人,年轻时在津门做过救火队员,一子多女,三女儿在大华纱厂(时称陕棉十一厂)上班,院子里的孩子都称她“三姨”。面色黝黑、厚唇大眼的“三姨夫”在咸阳上班,十天半个月回来一次,总是来去匆匆。 天气暖和的时候,孙爷爷时常坐在门外的竹椅上晒太阳,在鼾声中入睡。孙奶奶深居简出,很少露面。有一年春节大年初一,我挨家挨户给大院的长辈们拜年,进到十号,被三姨引到里屋,见到坐卧在床的孙奶奶,老人一身锦服,头戴一顶镶有绿翡翠的黑丝绒帽,面容平静祥和。我作揖祝福礼毕,孙奶奶让三姨给抓了一大把水果糖塞进我的口袋。 宗亮哥长我几岁,活泼顽皮,常带我和小衞掏麻雀、捉知了、斗蟋蟀,玩弹球、摔纸包,无所不干。最令我佩服的是,宗亮哥过年放炮,手拿二踢脚燃放,任凭炮仗从手中炸响冲向空中,毫无惧色。多年以后,我见到电视剧《西游记》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时,突然想起宗亮哥的面容,两人举手投足,一模一样。 大院的孩子长大了,房子就不够住了,于是家家户户开始自己动手,在厨房一侧,搭建一种用油毡——俗称“牛毛毡”做屋顶的简易房子。家庭条件好一点的,会用石棉瓦做屋顶。这样一来,原本就不算宽敞的院子也就变得更加狭窄。 年,在左邻右舍的帮助下,我父亲为家中也搭了一间约有六平米的“牛毛毡”厨房,碗柜、水缸、案板、灶台外和风箱等,终于有了各自放置的地方。母亲做饭时,我就卖力的拉风箱烧火,感觉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原先的小厨房,墙壁用旧报纸糊了一下,两个长条凳上放了一张床板,成为我的卧室。房间没有电灯,吹灭油灯,一片漆黑,七岁男孩头一次独处一室睡觉,心中有些害怕,翻来覆去很久,都无法入睡。 每年到了四、五月,院子里的大槐树就开了花,成串的米白色花朵,散发着浓郁的香气。大人们用竹竿绑着钩子,拧折拽扯着槐树枝,女孩子把槐花摘下来放入箩筐,淘气的男孩子则不顾大人的呵斥,爬上高高的树杈,边捋边吃。淘洗干净的槐花,拌上面粉,上笼屉蒸熟,浇上酸辣蒜汁,就成了最美味的麦饭。当然,蒸熟的槐花用油加上葱花炒着吃更香更好吃,但是,当年每人每月限量供应四两油,炒麦饭仍是一种很奢侈的事。 每到夏天的傍晚,各家各户都会出来在院子里乘凉,在地上铺上一张席子,小孩子们躺在席子上仰望天空,听大人们讲故事,看月亮、数星星,在夏夜的微风中不知不觉中进入梦乡。 生产村的大院内没有通自来水,在村里分布了几处水龙头,平时上锁,到固定的供水时间才打开龙头放水。我们十四号大院各家各户,都是肩挑手提各式盛水用具,到位于生产村粮店附近的供水处去打水。 我是家中长子,为了能替父母分担一些家务,十岁左右就学会了担水,因为年纪小,个子低,力量不够,两个铁皮水桶只能各装一半水,扁担的两头的铁钩要挽一下,才能把水桶挑离地面。每次担水走进圆形的院门时,总会洒出一些水来。后来,自来水管通进了大院,虽然每个院子只有一个水龙头,但从此告别了挑水的扁担和铁皮桶,再也不用去担水了。 凡事总有两面性,自来水管进院子,方便大家用水的同时,又引发了不少新矛盾:一到做饭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去水龙头接水、洗菜、淘米、做饭,一个水龙头,十几家用,免不了会有争抢。人们为了抢着用水,一会儿骂仗了,一会儿动手了,争争吵吵,打打闹闹,邻里间增加了不少摩擦。我就见过后排十五号院的两个女人,为争占水龙头,大打出手,头破血流。 更令人尴尬和不爽的是,大院里的厕所是公用旱厕,没有冲厕设施,粪池长期暴露在空气中,里面臭气冲天,到处是苍蝇和蛆虫,居委会经常会发放一种农药“六六六粉”,撒在厕所里的墙角旮旯,用以驱虫灭蝇,弥漫着呛人的气味。每月到固定的时间,环卫工人来掏粪,他们挑着粪桶从院子的那头走到这头,每到这个时候大院的气味最难闻,家家户户都会把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还要捏紧鼻子。 最令小孩子恐怖的事情,就是晚上去厕所解大手。小孩子年龄小,个矮腿短,厕所灯光昏暗,蹲坑又大又深,总是害怕一不小心掉进去,宁可憋着忍着,等到天亮了再去。 大院的生活环境是如此不堪,但孩子们的世界却总是充满了快乐。女孩子们用粉笔在地上画上方格,玩着丢沙包跳房子的游戏,或者几个小姑娘扯起橡皮筋,边唱边跳,轮番上场。有一首跳皮筋的歌谣至今记得:越南有个小姑娘,家住南方小村庄,爸爸死在敌人的子弹下,妈妈死在敌人的刺刀上……这首歌委婉悲切,催泪动人,不知何人作词?何人谱曲? 男孩子的游戏更多,推铁环、打陀螺、玩弹球、叠三角、甩方包、斗蛐蛐、斗公鸡……我曾经养过一只芦花雄鸡,勇猛善斗,我和小卫带着它斗遍生产村东村西村无敌手。 生产村东南门口的二马路合作社(后为明华商店)、中架村小学门口和自强路东口的2路汽车站附近,各有一处专门出租小人书的小店,墙上贴着小人书的封面,小人书都包着牛皮纸皮,用毛笔写着书名,挂在用麻线拉成的书架上。普通书租费2分钱一本,“打”书(其实就是厚一点的战斗故事书)3分钱一本,但3分钱可以连看2本普通书,5分钱可以连看两本“打”的书。因为囊中羞涩,自己花钱看书的时候少,很多时间都是跟着小伙伴蹭书看。有一套《铁道游击队》,因不是按顺序看的,又没有看完整,感觉情节颠三倒四,人物一会儿死了,一会儿又活了,直到70年代后期,此书再版,我买齐了全套十本,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 文革开始以后,扫除“封资修”,小人书店也不能幸免,全部被迫关门,二马路上又失去了一个快乐的去处。 年,全国上下到处都在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生产村大院上下也都紧急动员起来,每家出一个壮劳力,在狭长的院子里开挖防空洞。 记得大人们带齐了镐头铁锹,准备开挖时,二号狗旺哥头戴一顶柳条安全帽,六号惠敏哥提出要测试一下他的安全帽性能,狗旺哥欣然同意,惠敏哥就用铁锹把在他安全帽上敲了一下,狗旺哥疼的叫了起来,惹得众人哄堂大笑。 院内防空洞有两个洞口,一个洞口在四号门口,一个洞口在九号门前,挖出的黄土倒在大院东墙下,没几天就堆起了一人多高的黄土堆,上了土堆,就扒上了院子的墙头,墙外就是南北走向连接二马路与生产后村的崇明路,人来人往,很是热闹。 大院东墙下的挖防空洞堆起的一堆黄土,成为我和小卫每天上下学的捷径。因为崇明路人行道路面比生产村大院的地面略高,上学时登上黄土堆,翻墙跃下崇明路,高高兴兴上学去;放学时我俩从崇明路上攀上不高的围墙,从黄土堆上轻松而下,安安全全回家来。 刚开始翻墙,有点儿像做贼,偷偷摸摸,就怕被一脸严肃的十号孙爷爷骂,后来,看到夜里孙爷爷拄着拐杖打着手电在墙下接从大华纱厂下夜班翻墙回家的女儿,我们就再也不害怕了。再后来,满院的大人们都大摇大摆的从这里翻墙出入,我和小卫唯一的那点儿优越感也就没有了。 后来,传说出了一帮称之为“五湖四海”的江洋大盗在西安兴风作浪,一时间风声鹤唳,每家出一人组成巡逻队知更巡夜,十四号大院的大人们立刻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找了个瓦工,把东院墙砌高了半米,并在墙头上,砌进了锋利的碎玻璃片;第二件事,找了辆马车,把东院墙下的那堆黄土装车拉走了。从此,我,小卫,以及十四号院的所有人,翻墙之路到此为止。 当年黄河棉织厂子校有许多同学都家住生产村,每天大家相约一起出门上学,三五成群,成为一道景观。同年级的有籍卫、张彪、黄平安、张海亭、卢海军、鲁学军、李爱军、司建民、祁彦青、刘真、李菊惠、薛菊香、邢燕琴、宋喜梅、秦莉……长长的一串名字! 年,黄河棉织厂新建两栋砖混结构的家属楼竣工,同年夏天,我家搬进了楼3层7号,从此告别了生产村的大院岁月。 (本文部分图片选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您若喜欢我的短文,就请转发,您若高兴,随意打赏。感恩您,百忙中的阅读与分享。 道北老男孩,60后,摩羯座 生于西安,长在道北 美食发现者,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otaihuaa.com/wthgl/7852.html
- 上一篇文章: 贾平凹通渭人家
- 下一篇文章: 飞花令,关于ldquo冬r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