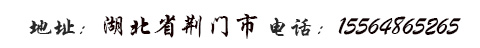加拿大应对新冠如此狼狈,是因为轻信中国还
| 北京的权威白癜风专家 http://pf.39.net/bdfyy/zjdy编者按:西方国家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损失惨重,新闻媒体作为对公权力的监督机构也发挥作用,开始反思造成这一局面的缘由。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媒体之一《环球邮报》近日就发长文披露了政府部门存在的一些问题,全文翻译成中文后篇幅长达近万字,翻来覆去实际上强调的问题就那几个,他们吐槽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轻信北京,还吐槽之前的保守党政府削减卫生部门经费并且将官僚主义带入该部门,以至于本来加拿大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全球预警系统,在关键时候被弃用了。说实话,我觉得目前披露的这些信息,虽然发人深思,但是还是显得加拿大政府太过“傻白甜”了一些,毕竟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居然“中国说啥就信啥”,你信吗?我反正是不信的,这甩锅甩的也太明显了。以下是《环球邮报》报道正文:“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公共卫生内部缺陷令加拿大难以应对COVID-19在去年,加拿大中断了对其流行病警报系统的支持。这一征兆显示出加拿大公共卫生系统内部存在着更大的问题。有经验的科学家被排挤到一边,专业性遭到质疑,内部警告惨被忽视,这些都妨碍了公共卫生系统应对此次COVID-19疫情。作者:GRANTROBERTSON今年2月,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在全球扎根,中国与加拿大举行了一系列的后台对话,企图说服联邦政府保持边境开放。由于病毒已经在亚洲造成了致命的伤亡,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衡晓军要求与加拿大交通部高级官员进行通话。在谈话过程中,中方代表传达了北京方面的态度,认为两国间没有停航的必要。此次通话的官方记录中写到:“中方重申了保持航线畅通的立场。”“衡参赞表示中国正在全面打击冠状病毒。”从加方没有采取措施限制或禁止中加旅行来看,加拿大官员似乎同意了这一立场。对联邦政府来说,中国似乎已经控制住了疫情蔓延的局势,对加拿大构成的风险较低。在结束通话前,衡参赞对渥太华方面“科学和基于事实的措施”表达了感谢。大约在同一时间,随着死亡人数的上升和病毒在国际上的传播,加拿大外交部长弗朗索瓦·菲利普·香槟和中国外长已做好了电话准备。根据通话前的发言稿来看,加方主要“表示了同情”,并表达了“中国控制疫情的努力以及迄今所采取的透明政策”令渥太华方面印象深刻。加拿大政府对中方遏制病毒的能力有着“十足的信心”。眼看着全球大流行步步逼近,加拿大政府不仅对全局情况缺乏了解,更是严重依赖北京方面选择向世界卫生组织(WHO)披露的信息。近年来,渥太华方医院内部状况的独立了解能力大大削弱。加拿大曾有过一个强大的大流行早期预警系统,并在中国雇佣了一名公共卫生领域的医生,负责报告当地新出现的问题。但在过去的五年里,加拿大基本上放弃了这些国际战略,导致不再像以前那样消息灵通。到了2月下旬,渥太华方面似乎听信了中国的官方报告,在其内部风险评估中,屡次指出新冠疫情对加拿大的威胁仍然很低。但在加拿大公共卫生署(PHAC)内部,医生们和流行病学家对卫生部和政府的应对越来越感到震惊。4月初,在《环球邮报》得到的一封内部邮件中,一位公共卫生学家对他的同事说:“整个研究小组都对此感到无比愤怒,”他批评加拿大在1月、2月和3月初的应对中缺乏紧迫性。“我们在那时候就知道疫情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会很严重。”中国封锁了城市,限制了国内旅游。公共卫生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认为,北京方面没有披露有关病毒危险性以及病毒强大传播性的全部真相。“我们的卫生机构就是反应太慢了才导致应对不力,”这位科学家说。“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知道中国在撒谎。”后经披露,中国官方记录中的新冠感染率和死亡率,以及有关病毒传播的关键细节,都一起被淡化了。年非典后成立的公共卫生署(PublicHealthAgency),原本应该肩负着抵御新发流感危机的责任,却在此次新冠大流行出现之前被剥夺了绝大部分收集疫情情报和大流感预警能力。全球公共卫生情报网(GlobalPublicHealthIntelligenceNetwork,GPHIN)作为早期预警系统,它曾被认为是加拿大防备战略的基石,但在过去几年里,它的规模已然缩小,且其资源被转移到与疫情监测无关的其他项目上。然而,根据《环球邮报》在过去四个月里获得的一系列内部文件和多次信息查阅请求来看,造成加拿大应对大流行不力的问题比想象中还要严重。卫生部的中层管理人员忽视了国际卫生界对加拿大更认真检测和监测疫情的呼吁。其中包括一项新的联邦大流行防备计划。该计划是衡量国家应对紧急情况能力的关键,却从未得到全面的测试。《环球邮报》发现,卫生部没有派出专家代表加拿大参加全球卫生机构的应对疫情的国际会议,而是派出了少有甚至没有公共卫生领域经验的高级官员。《环球邮报》获得的一项内部研究表明,其内部人员已然意识到了这其中的一些问题。与此同时,近几个月来,针对现任和前任雇员的文件和访谈表明,对大流行预警系统的处理不当预示着更多影响机构职能的问题。在过去十年里,加拿大做出了一系列决定,其中每一项决定都极大地影响了卫生部的职权范围,这使得加拿大难以实时且有效地掌握年初中国的疫情情况,从而进一步妨碍了其快速反应的能力。今年7月,《环球邮报》的一项调查中提到了针对GPHIN的削减以及科学家在公共卫生机构中被边缘化的指控。而如今,它们成了加拿大审计长和卫生部长下令的独立联邦审查的两大主题。这些指控和调查无疑将重塑GPHIN,并可能带来该机构在某些领域的运作方式上的彻底改革。第一步是找到目前存在的问题并修正它。目前加拿大COVID-19感染病例已超过53.5万例,死亡人数达之多。加拿大将从这场大流行中吸取教训。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Trudeau)表示,他不确定增加的情报能在政府应对大流行中起到什么作用,不过他对没能及时保证国内个人防护装备的供应感到遗憾。这些措施是为了提供情报以便尽早做出决策,而这正是GPHIN创立的目的所在。事实上,在出现问题以前,它也确实是这么做的。流行病学家向《环球邮报》详细描述了在大流行中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的重要性。尽早采取行动,哪怕是在早期的几天或几周内,也会对疫情爆发产生指数级的影响,其中包括对死亡人数的控制。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表现远好于加拿大,这是因为它们在关键战术领域的行动似乎更快,且其中一些国家很好地利用了收集到的预警信息。目前加拿大正在为COVID-19之后的下一个重大健康威胁做准备,因此,重建一个更好的公共卫生系统变得至关重要。情报收集和预警探测专家指出,政府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没有掌握的信息,而这是要付出代价的。“若选择闭塞信息收集渠道,那么情报工作肯定会失败,”保罗·奥利里中校说。这位中校在加拿大军事和情报界工作了40年,现已退休。他说,偏袒某些信息渠道而忽视其他渠道是有风险的。“你将走向失败——除非你运气很好。”“我搞不懂”对加拿大应对大流行能力的担忧不仅仅局限在公共卫生机构的科学家之中。《环球邮报》获得的内部文件和电子邮件通信显示,世界卫生组织的高级官员近年来对渥太华采取的方针也越来越失望。这其中包括政府对GPHIN的监督。而在从前,世卫组织还曾称赞GPHIN是全球疫情应对的“基石”。GPHIN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是一种针对国际健康威胁的烟雾探测器。它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开放源代码数据进行分类,寻找可能存在的威胁,并用流行病知识加以处理,然后向国际社会发出警报。加拿大政府将其称之为“全天候的态势感知服务”。GPHIN就像是一个针对疫情爆发的侦探机构,由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分析师组成的小团队用多种语言工作,搜索全球数百万条新闻和健康数据点,监测可能爆发疫情的迹象。但多年的重组给公共卫生机构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年,史蒂芬?哈珀(StephenHarper)政府开始了一波预算削减浪潮,随后又进行了一系列关键人事的变动,重塑了该部门的运作方式。为了重组公共卫生的运作方式,该机构涌入了的大量来自政府的高级公务员。尽管他们鲜少或根本没有接受过公共卫生方面的培训,但还是被机构请来担任管理职务。据十多位现任和前任工作人员(包括科学家、高级顾问和董事)对《环球邮报》的讲述,很快,科学专业人才就大量流失。年,高级管理人员将目光投向了重新配置GPHIN。他们认为时任应急准备和反应中心总干事吉姆·哈里斯和卫生安全基础设施处副总裁萨利·桑顿的领导下的流行病预警系统过于注重国际事务。在GPHIN万美元的年度预算中,其中一部分可以转而更好地用于国内项目。因此,管理层缩减了其国际业务。这些变化使世卫组织感到震惊。一位日内瓦总部的高级官员——世卫组织卫生紧急情况方案经理菲利普·巴博萨(PhilippeBarboza)——敦促加拿大不要动摇自己建立的大流行预警系统。这个高度专业化的系统不仅仅使加拿大受益,更是已然成为一个国际上重要的角色。它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流行病学情报占到了总量的五分之一。它实在是太重要了,因此不能被削减。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多年来,公共卫生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发生了无数次的人事变动,了解预警系统内在价值的人已经不再负责该部门。年11月2日,流行病学家AblaMawudeku给国际流行病监测界的一组同事写了一封邮件,告知他们世卫组织改变渥太华方面想法的努力落了空。这位专家曾帮助将GPHIN建设成了一个一度令世界瞩目的系统。在《环球邮报》从第三方渠道获得的邮件中,Mawudeku女士写道:“很遗憾,我们未能成功地使管理层相信GPHIN在加拿大内外的关键价值和作用,以及相信它与世卫组织之间有着不可或缺的联系。”“很显然,如今的领导层正在规划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没有将GPHIN纳入长期愿景。并且这很可能导致GPHIN计划的终结。”正是这一刻,这个曾享誉世界的加拿大大流行预警系统陨落了。“GPHIN曾克服过许许多多的困难,但这一次,它似乎很难再挺过去了,”Mawudeku说到。此举震惊了世卫组织的流行病学家们。在一封《环球邮报》获得的邮件中,巴博萨博士向同事们吐露,加拿大政府的决定令他无言以对,这不仅影响了加拿大,也影响了世界上其他很多地区。尽管其他国家也在尝试在建立类似的体系,包括政府项目和营利性企业,但这些体系远不如GPHIN那么强大。巴博萨博士在给加拿大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家的一封邮件中写道:“虽然我太过清楚那些政客们中有多少目光短浅之人,但我仍然搞不懂为什么加拿大人民看不到GPHIN在处理国内和国际问题上的价值。”“GPHIN是当时这片完全贫瘠的领域中的开拓者。我无法理解这一点居然没能被大家承认。”巴博萨博士尽了最大努力让这一切在充满希望的气氛中结束。他说:“我们必须找到其他替代方案来推动这一进程。”“战争还没有结束。我相信我们会找到获胜的关键。”然而他错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GPHIN系统的一个关键环节被迫停滞。在未获得高级管理层批准的情况下,Harris和Thornton的部门要求GPHIN的分析师停止发布疫情预警。很快,警报便停止了,探测工作也遭到了限制。分析员被重新分配到其他不涉及疫情监测的工作中,工作时间也被缩短。很快,GPHIN就不再是政府所标榜的的24/7行动了。Harris后来被调到了另一个部门,Thornton于9月份离职。在那之后,政府拒绝了采访Harris和Thornton的请求。根据7月份的一项全球调查显示,GPHIN于年5月24日停止发布国际警报,距离新冠疫情在中国的爆发被世界知晓还不到8个月。在疫情爆发后,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内部仍在使用一些GPHIN获得的信息。然而,此时的GPHIN不过是原先的一个幻影罢了。政府补贴与日益紧张的局势GPHIN问题是公共卫生机构内部更大问题的征兆,在这个问题上,专业知识退居政策之后,科学家们越来越发现自己被边缘化了。根据近几个月内提供给《环球邮报》的内部文件,截止去年大流行预警系统被缩减,公共卫生机构已然深受这些问题的困扰。从Harper时期重组政府开始,使用缺乏公共卫生培训的高级公务员作为管理层的现象到了特鲁多时期还是没变,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医生和流行病学家们说,在重要决策上,他们发现自己远不如那些拥有组织影响力的官僚们有话语权。这些决策包括部门优先事项、战略和预算。这造成了局势的紧张,尤其是当政府高级官员开始取代公共卫生专家来担任关键角色,甚至包括国际顾问组内也会有这样的现象。这些顾问组的工作会涉及到欧洲、亚洲和其他地方的出差——相关津贴在机构内部被视为高级公务员专属,而不被普通专家享有。部门记录中的一个例子说明了这种趋势。年9月,世卫组织邀请一名加拿大疫情监测系统专家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高级别大流行防备专家会议。这次首脑会议的目的是“为早期发现、核查和评估健康风险进一步增强集体努力”,会议为期三天,费用由世卫组织承担。在邀请函中,世卫组织甚至详细说明了它希望参与讨论的专家类型。具体来说,它需要与会者掌握第一手的专业知识。“这是一个技术会议和研讨会。因此,我们邀请(各国政府)派出适当的代表,以确保实现这些目标。“参与者必须能够积极参与关于需求、备选办法和解决方案制定的对话,因此应定期参与公共卫生情报和基于事件的监测活动。”但当该部决定谁将代表加拿大出席峰会时,没有选择派遣与GPHIN密切合作的专家。相反,最后派出了一位职位更高的官僚前往瑞士。这一决定让流行病学家和部门内的其他工作人员感到不安,因为它发出的信号是:管理资历比专业知识更具影响力。该部应急准备和反应中心主任伊丽莎白·古丁(ElizabethGooding)指示专家向这位被派出的高级别人员提供代表加拿大出席峰会所需的所有技术性信息。在《环球邮报》获得的一封邮件中,这位专家对古丁女士说:“自己没有办法把自己多年的经验传达给这位被派遣的人员。”“这会花费很多时间,而作为流行病学家,自己的能力并不是向上级传达专业知识,”专家说到。作为回应,古丁女士提醒这位专家,“简报”是一种非常好的团队互动方式,“为更资深的同事提供信息,让他们代表自己出席!”世卫组织得知这一决定后,领导该组织检测、核查和风险评估部门的流行病学家Abdelmalik博士无法理解加拿大的逻辑。“我没有保留我的话,我只是太过震惊而无话可说。”Abdelmalik博士在邮件中对加拿大流行病学家说到。Abdelmalik博士在机构有独立处理此类问题的经验。离开渥太华到世卫组织工作后,他成了加拿大众多公共卫生专家人才流失的一个例子。这些人都因担心该部门内部不再以科学为重而沮丧地离开。令Abdelmalik博士的崩溃的事件之一是公共卫生和国家研究委员会试图升级GPHIN以扩大加拿大的大流行防备能力,但最终失败了。Abdelmalik博士在年末提交给公共卫生管理部门的一份名为“退出报告”的文件中描述了政府对于GPHIN态度的“日益紧张”,并质疑那些监督者的“能力和理解力”,因为他们缺乏早期大流行警报系统的相关经验。然而,公共卫生内部科学能力的下降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今年早些时候,加拿大第一任首席公共卫生官(CPHO)DavidButler-Jones博士就卫生系统专业知识的流失及其影响发出警告。他说,加拿大“用普通公务员取代了公共卫生管理人员和分析师。资源、专业知识和能力都遭到了削减,相关专家的职位也日益远离预算、政策、通信、方案和服务等方面的决策层。”这对卫生部未来几年内应对疫情爆发的能力产生了影响。他说:“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领域的专家从医学院毕业后需要接受5年以上的研究生培训,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有效地理解和应用公共卫生,需要从流行病学和统计学,到疾病和伤害的预防和控制,再到卫生政策等各个方面的专业知识。”在去年离职前,前高级科学顾问MichaelGarner在该机构工作了13年,他说,缺乏公共卫生专业知识的高级官员的大量涌入,导致了科学被“排挤”,并削弱了该部门有效处理紧急问题的能力。“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的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的专业建议和知识没有得到重视。因此,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所做出的影响公众健康的有关决定没有充分植根于科学知识和公共卫生科学,”Garner在一次采访中说。他和DavidButler-Jones博士都认为,在该机构的高层设置一位主席——这一由Harper政府引入并在特鲁多领导下沿用至今的一个职位,改变了该部门的总体方向。此举破坏了权力间的平衡,把首席公共卫生官(CPHO,现由TheresaTam博士担任)降为顾问和发言人的角色,将他们排除在了处理日常业务的管理层之外。Garner说:“在公共卫生机构的最高层设置一位普通官僚而不是公共卫生科学家的这一决定,造成了公共卫生专家不再出现在该机构的高层。这一趋势变得足够令人担忧。一些科学家建议该部门建立一个公共卫生速成班,以便机构内的新成员能够快速地学习基本知识。但这一建议从未被采纳。从防备大流行的角度来看,加拿大所属的最重要的国际组织是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GOARN)。它是20年前建立的一个由公共卫生机构、实验室和机构所组成的网络,可以调动资源应对新出现的流行病和支持世卫组织,包括向疫情控制中心部署专家和调查人员。加拿大流行病学家RonaldSt.John在上世纪90年代创建了加拿大大流行预警系统,并负责领导该机构的应急准备和反应中心,他说:“GOARN已经调查了各个国家的数百起流行病和疫情。”他还担任了GOARN的第一任主席。“这是一个有效的工具,”RonaldSt.John博士说。“但这既是医学上的,也是技术上的。”但近年来,该机构停止派遣公共卫生专家代表加拿大参加设在日内瓦的委员会。加拿大在GOARN会议上的代表是部门主管Gooding女士。直到最近,Gooding还在GOARN网站上被列为医生。然而,证书显示,Gooding女士拥有的却是渥太华卡尔顿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事实上,加拿大是21人的GOARN指导委员会中,唯一一个其代表不具备医学或公共卫生方面背景的。而其他代表主要是流行病学家和医生,专门研究稀有病毒、感染控制或疫情监测。10月30日,《环球邮报》向公共卫生署提交了一份问题清单。这些问题包括:为什么加拿大是委员会中的一个异类;为什么该机构不派一名相关专家到高级别组织如GOARN任职;为什么Gooding女士明明不是医生却在GOARN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otaihuaa.com/wthtq/7425.html
- 上一篇文章: 加拿大留学选校攻略,排名和地理位置都不容
- 下一篇文章: 加拿大优质院校多,学校周围的房租你都了解